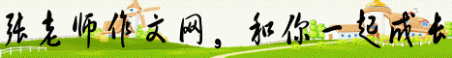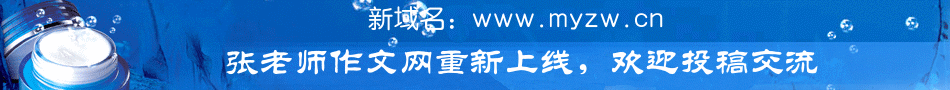牵丝戏
徐骢
花开为序,幕落为歌。花开之后,终是暮落。回忆如雪花般翩,蓦然浮现。
少时,约莫三四岁,那时的孩捉对世界充满好奇。我住在叔婶家里头,自是受二叔影响颇深,他爱看戏,还是牵丝戏。“他常说:“唉,二十年的岁月末至,怎就将这国粹湮没了呢……
依稀晓得有个戏班在常盛街头 卖艺谋生,叔是常客,我自然跟着前去罢。
落日的余晖褪尽晚霞最后一抹醋红,灯火幽微之际,三尺红棉台毯一铺,三两个棚头傀儡粉墨登场。街头周围的人倒都拿个小板凳簇拥前来。前排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小丫头们,后排看不清的就骑在爷爷奶奶的肩膀上,像得胜的将军一样,两条腿在胸前晃荡。
但随着一戏班第子的叫板声响起,喧闹的四周突然变得安静了,隐约能听到呼吸声,只留得戏声在此打转。从花木兰到杨家将,从卓文君到杜丽娘,唱腔有些许沙哑,不复圆润却饱含沧桑。一到戏眼,总得先顿一下,而后又激情澎湃,更是铆劲发挥。幕前,人偶舞步阑珊,一颦一笑,似乎真带上了伊人的风情。而戏腔声越来越大,耳畔脑际恍有毛发耸立;幕后戏子双手变幻,舞得龙飞风舞,一身功力皆淋漓尽致。
回龙腔过后,蓦然声散。人人都呆愣在原地,对世界忽然感到陌生了。而后,戏幕在一片叫好声中华丽落下
现如今,却已无人欣赏这宏伟国粹;如今再无人在意那圆润的戏腔声中愈发的沙哑、悲怆。如今,已无人知晓戏班的去处……大戏台已被水泥铺成了大马路,清脆悦耳的盘铃声也被立体环绕式音响替代。也许,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戏子早闭上了绝望黯然的双眼,颤颤巍地将那戏具扔进火炉。一生牵丝弄线,相依为命,却在“哔哔剥剥”的响动声中,看着火光舔过一身绮丽舞袖歌衫,燎尽椴木雕琢的细巧骨骼。难道,这份传承就真后继无人了吗?
唏嘘一句,可惜可惜!
幸好,这些天,知晓国家开始重视起这绚丽奇观。恍惚间,我透过窗外,好似又听见那几声唱腔从历史回归传承。
能记得——
落花千树,星落如雨。风箫声动,锦瑟乐起,娇娥舞始。笑语盈盈,勾人心弦。
犹听闻——
西风飒飒,桐叶萧萧,骤雨狂风至。在离亭,月胧明,只闻孤雁惊鸿语。
也见得——
塞外点兵,吹角连营。夜深星阑,挑灯看剑,长驱直入,大破五万军。风雪卷刃,只留得染绣金戈。
一幕幕悲欢离合,一曲曲悲扬婉转,一声声烟火阑珊,仍道不尽世间百态。戏,原早已与我血脉相融,骨肉相连,烙印在三魂七魄中。苒苒萌物华虽不可追。
只愿:昔日门庭若市不只是昔日风云,昔日千古吟唱能继续传唱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