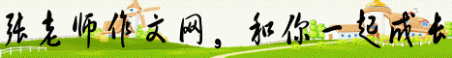《太》
经过一条狭长的村道,两旁鹅棚叫声不绝。
于是,整个村的人都知道有人来了
因为路窄,车,远远的,停了。远远的,我也看见了房顶上的一片灰绿。
留在本村的人大都与那榕树一般老了。自从北面的臭水沟被填了建起工厂,村子里才渐渐多了些莫名的生气。
那片灰绿愈来愈大,终于,见到了那老榕树的根了,噢,我们也快到。
背着榕树下那熟悉而陌生的眼神,拐过几个弯,钻进了那比我肩略宽的小巷,嗯,到了!
窗子很低,窗沿大概到我的眼睛那么高吧,于是,我们还没进屋,里面的人就知道我们来了,不出所料,
恭喜发财,快高长大之类的话语来往一番,我便在门边的小木凳上坐下,长方形的小客厅本来就不宽,这么多人都挤在这里,多少有些拥挤,但,又何妨呢?
客厅那头,神柜那角,有台比我的脸略大的电视,与它连着的天线格外夸张,但也只能使电视接收到一个频道……“随便啦,反正看不懂”
以往在电视前发呆的身影忙碌着,一个个红包包着太多太多的喜悦与幸福,那薄薄的一层红纸“吹弹可破”,里面,也就两张皱巴皱巴的一元吧?但那两张一元再老旧,也老不过她,旧不过她。
环顾四周,青砖,灰瓦,马赛克地板。天花板上那一片大大的水迹讲述着这里的当年,早就被熏黑了的厨房旁有个崩了盖的水井,这会是我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的水井吗?房子很小,小得我都不知道她谁在哪,直到那么一次,我进去“黑房间”里拿胶袋,才在昏暗中看见一张,白帐红褥的床……
余光中,那红得新亮,新亮得与屋内的一切都不相衬的对联引起了我的注意,写什么忘了,大概寓意长寿什么的,字,是手写的,稳重而浑厚,工整而苍劲。正看着,她从厨房柴堆里一步一步地出来了,走得生硬而勉强,看着都心疼,而她,把一切的欣喜都堆在了脸上,就像长辈拿着玩具在逗婴儿开心那样的欣喜:“啊。。。航。。。你上次来的时候。。木头。。。是不是?。。呵呵。。啊?呵呵呵。。。”我怔了下,才反映过来:去年我来访时因贪玩找她要了把柴刀砍了一截路边的枯树枝,想用来当弹弓还是木剑什么的吧,刚削了树皮,便得走了,匆忙间,我把树枝藏了起来,来年再削!可……面对这半盲半聋、年及耄耋(mào dié)的她……连我都忘了这事,她却记着一年!
我边吼着:“是啊!是啊!”边接过木棒,扶她坐下。。。我拿着摆弄了几下,又放回了柴堆,心里总有种难以言表的感觉,为什么呢?
我收起了手机,三姑六婆们的嚷嚷顿时充斥了我的整个世界,在她们的回忆中,我才知道她是个倔强的人:
她,会为了家用那保不住骨的皱手不顾一切,徒手拍死一只大老鼠;
她,会为了保住门前的老井,不让它被填了,在那井盖上披上一件薄衣,坐了一天一夜。
她曾是大家闺秀,姓黄名金;她,曾丧夫丧子,风雨交加,独守空房;她,曾是一家之柱,教子孙行正学高……她威严,我的母亲深受其影响,个中滋味我知,她坚强,熬过文革土改,面无惧色。
她,有着我无法想象的传奇与神秘。
我总不会忘记每年中秋佳节庆贺诞辰时的盛宴,我是如何吃滚圆了肚皮,而我,却连为她洗碗都洗不好。。。(村子里有个补锅的用那不知名的物质替她补了个碟,看似口香糖,我把它抠了,她舍不得浪费,心疼了好久。。。。)
多年前记录着她笑容的记忆卡,最近才发现弄丢了,当我考上了艺高,南海七校之一,她了,而我,却还没来得及为她亲手画一幅肖像。。。。。。
她,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,我太婆,白话里,我叫她:阿太
如今,她早已离我远去,也离众亲友而去,凭生前之功德,我相信,她总会上天堂的。。。。
墨迹至此,涕泗横流,呜呜声,不绝于耳。
翻开那红包,两张崭新的五元蜷缩于其中。
我。。。。
唉。
第二稿
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