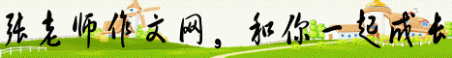核心提示:我把木子称为“木子哥”是在省城按揭买房的那一年,木子拿钱给我交了首付。叫了二十多年的“木子”,一下子改过来,嗓子眼硬生生的,感觉格外的拗口和别扭。因此,在众人的场合,我会把“木子哥”这三个字尽量加快语速,含糊不清,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到。而木子却能够在人声嘈杂中准确地听出来,这样没有人注意到我这敏感的...
从大村到乡集市,原先没有修公路,一条十二指肠般的小路麻绳缠般绕着七座高山和三条大壑。木子每次卖羊,得起个大早,腰挂小壶,挎包塞些干粮,便赶着羊翻山越岭,到达集上,卖给羊贩子。起初是赶几只、十几只、后来几十只,羊的数量增加,赶羊的伙计也增加,防止羊在路上“掉队”,去时浩浩荡荡,回来时欢欢喜喜。
木子卖羊吃过亏,那一次经历可没有忘记,一直以来称羊称都是大杆称,木子认得斤两,称时把羊绑起来吊着称,每称一只木子就在小本子上歪歪斜斜地记下来,最后把重量加起来,再计算该拿多少张,每次木子都要重复几次,没有什么差错。但那一回,是暑假,羊贩子换了把没有见过新磅称,把羊赶到大称板上称就行了,称上做了个大笼子,一次可以称很多只,很方便。而称标尺上标着“5kg”“10 kg”之类的,木子不懂“kg”是什么。称出“158 kg”,羊贩给他九张大团结,他觉得不对劲,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,便把“kg”画在本子上,回来问我。我说:“kg ”就是千克,一千克就是一公斤,一公斤就是两斤……”。说到斤他就狠狠拍了一下脑袋,叹息着。他又算了一下:158千克等于316斤,每斤毛羊肉3元,应得948元。那兔崽子少给了48元了。从此,他卖前多了一个心眼,如果称杆不平衡,和同羊贩论理,每次出发前,把每头羊一一抱了一遍估摸一下重量。然后把割好的肥草喂,给将卖的羊儿大吃特吃,喂好水,增加些重量,可是他还是有埋怨,那羊是边吃边撒,他是边喂边骂,恨不得用木塞住。卖完拿到钱,正数三遍,反数三遍,仔细瞅瞅,仔细摸摸,有没有假钱,再放到自制的帆布包里扎紧包口。小心翼翼地走去信用社存起来。妥当了,邀着伙计们去路边小酒馆喝几盅低劣的玉米,那酒便宜。回来时,面红耳热,每次不忘给父亲捎来一瓶瓶装酒,他不喝瓶装酒,说有马尿味。
我毕业的时候,大村到乡集市的村公路已经修通,并浇上厚厚的沥清,穿梭在大山大岭间,木子不用早早起来,装粮备水去赶羊卖了。羊贩子羊圈般的货车隆隆开到大村的榕对下,那是木子出生的地方,也是距离十里湾羊圈最近的地方。老人小孩坐在树下,观看那些奇怪山外人,说很奇怪的话,大村人听不懂,上过学的年轻人偶尔明白几个句。子卖羊时,也只得边说边比划,待双方明白了意思便哈哈大笑。也就在那一年,木子从邻村带回了一个女的,说是要结婚了。
年关,我回老家,中巴客车开到村里去了,榕树下的平地形成了一个小车站,平整成水泥地,几辆车参差不齐地停在那儿,大卡,小卡,双排座,单排座,平头,子弹头……车门上喷着:寒水乡岑黄大村。宋体字,工工整整的,格外醒目。水泥地一端正值召开村民会年终总结大会,村民们歪歪斜斜坐在下面,斗眼爹坐在主席台中间对着话筒讲话,点了一长串名字。都是养鱼养虾养乌龟王八的,张三娶媳妇李四盖房子的,又讲到捐款建学校的事。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木子,他坐在主席台后排最末端的位置,还是那的黑,那样的瘦,只是衣着很光鲜,腰间别了一部手机,脸上呈现了一些麻子,虽然我们年龄接近,但他明显老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