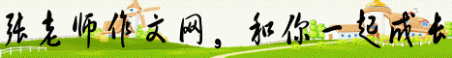核心提示:她抿了口酒,酒流入喉咙里,呛到她的神经了,于是,她便不停的咳嗽起来。 霓虹灯亮起来了,珠灯下,像满天的繁星,亦像名贵的珠链。 眼珠在这殿堂般的舞厅徘徊了一阵,这里很美,她知道的,而且很清楚,自己与这的美丽是格格不入的。她拉了拉裙角,不自在地耸了耸肩,叹气,吸气,似乎在准备着她的准备。 音乐播起来了,...
她抿了口酒,酒流入喉咙里,呛到她的神经了,于是,她便不停的咳嗽起来。
霓虹灯亮起来了,珠灯下,像满天的繁星,亦像名贵的珠链。
眼珠在这殿堂般的舞厅徘徊了一阵,这里很美,她知道的,而且很清楚,自己与这的美丽是格格不入的。她拉了拉裙角,不自在地耸了耸肩,叹气,吸气,似乎在准备着她的准备。
音乐播起来了,现场的乐队,气派,萨克斯的温柔,一个个陌生的嘴脸都踩着音乐的节奏在舞池上扭动起来。
有人邀请她对舞,她拒绝了。因为,她知道的,无论是华尔兹的优雅,还是伦巴的热情都是她无法驾驭的。脚下的高跟鞋割痛了她的脚,拿鞋去穿的时候,紧张的她,一时弄错了码数,鞋子偏小了一码,穿在脚上,每走一步,都是有如灌铅了般的沉重。
另一支舞曲播起来的时候,又有人邀请了她入舞。她还是拒绝了,她试图让自己表现得优雅些,于是学着电影里的那些有钱人,她成功了 ,即使每步走出去都带着痛,但是她还是那么美,比起那些用名贵化妆品画出来的女人,更加带了些高傲,更加带了些脱俗,但是又不失纯真,对,不失纯真,她想着,灯火迷糊了。
拿了杯酒,她移步到落地窗前,望去,俯瞰,这个城市是那么美,她开始动摇了,她在想,她是否要动摇,因为毕竟这个城市,有过让她如痴迷的人,但是又是伤她做深的人。她于他,不外乎是一件工具,甚至连工具也不是,只是一个玩物。
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来这里,或许是在服装店里捡到那份舞会的邀请函开始,她便有这个打算;或者是,是她想感受一下自己从来就没有感受过的生活,了却心里的遗憾;又或者是,她知道,她曾经最痴迷的人,今晚也会出席这舞会,她不过是想问他一句,或许是这辈子最后的一句:你爱过我吗?她想她是应该知道的,这样,她才会没有任何的牵挂,即使,知道,现实会让她心死去。
霓虹灯转,人也开始有点迷离了,落地窗外,城市也醉倒在这样的热闹中,只有在人外,才可以把自己看的清楚,她知道,她算是什么?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小市民。
舞会的主人是一位气质很好的少妇,保养得十分好,鱼鳞闪片的晚装,加上挂在她脖子的,不知道多少克拉的钻琏,她知道,这就是她和这个舞厅的人的区别,她想,她是一直都明白的。只是有过这么一会,她糊涂了。
她不过是服装店里的一名小售货员,每天的工作,也不过是伺候别人穿衣买衣。但是,其实她并不曾在乎的,因为她一直在期待着,上帝是会眷恋她的,只是迟早而已。真的,上帝开始注意这个可怜儿了,可是美好才开始,上帝就去打盹儿了。男朋友不过是贪图她的美色的人,玩完,玩腻,就把她扔掉了。她相信真感情,但是,自己就成为了有钱人的游戏了无聊玩物,而她在在这个无聊的游戏里,投注了她的真感情,甚至是她的贞洁。
她看到他了,他挽着一位浓妆艳抹的性感女郎,女人被华丽的晚装包裹出骄人的曲线,但却是一个带着面具的虚伪女人,或许这样的女人,在这些场合活着,才不会那么累,也才适合在这些场合活着,像墙头草。而他在女人的耳边说着悄悄话,然后又转向他的那些朋友,大肆地说着他们圈子里的黄色笑话。纸醉金迷里的人群。有钱的人笑了,其他的人也会笑;更加有钱的人了,有钱的人也笑了,其他的人才也笑了。没有人尝试掂量这些笑容的重量,或许就知道,这不过是轻于羽毛的重量,不值一提。又或许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游戏里的规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