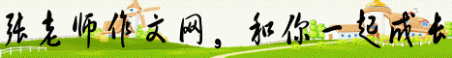核心提示:我把木子称为“木子哥”是在省城按揭买房的那一年,木子拿钱给我交了首付。叫了二十多年的“木子”,一下子改过来,嗓子眼硬生生的,感觉格外的拗口和别扭。因此,在众人的场合,我会把“木子哥”这三个字尽量加快语速,含糊不清,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到。而木子却能够在人声嘈杂中准确地听出来,这样没有人注意到我这敏感的...
长齐牛屁股那么高时,我就到乡小学念书。木子也被父亲送到乡建筑队做“土工仔”,和大人们一起搅水泥,挑石砖,维持生计,他也能自力更生了。他们还给乡小学修建教学楼。在烈日下,木子黑成了一截被烧过的木桩,一根扁担压在肩上,咯吱咯吱响,晃晃悠悠,悠悠晃晃地走,挥汗如雨。我问他:“累吗?”他说:“不累”。憨憨一笑,“以后也给大村建一个。”在我缺钱短粮时,父亲不能及时供给时,他准会出现,塞个三块五块,并笑笑说:“节约用”。那时三块五块已经是半个月的生活费了,我并没有谢谢他,因为觉得家里曾经有恩于他,他应该这么做。
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,大村的人都为我沸腾起来,这是大村考上的第一个大学生,大村人都因为我而脸上有光。父老乡们亲堵到我家门口,道贺的道贺,恭喜的恭喜,热闹非凡,父母亲却骤然乌云密布,乐不起来,这高昂的学费就是把老祖宗卖了也凑不齐。可敬的乡亲们便一角两角,一元两元地捐助。满含热泪的母亲千谢万谢。我在柴房里,默默地劈柴火,默默地切猪食。开学临近了,学费还没有边,不知如何是好,我们只得作复读的计划。大家飞都没有办法的时候,木子乐癫癫地奔回来了,急急忙忙地说:“学……学费……不用愁了。”大家面面相视,愣神儿,木子又认真地说了一遍,父亲说:“咋不用愁?”他从兜里抖出一砣旧报纸,小心翼翼地打开,果然是一堆钱币,我们愕然极了。木子说这是他几年来吃辛吃苦积攒下来的钱,本要留着盖房子,娶媳妇的,现在先交学费,上大学是光宗耀祖的事,比媳妇重要。这下让我们和大村的乡亲们觉得木子就是大村的土地神,大村人很少看到一个人有这么多钱。木子在我们心目中换了个人似的,木子便不再是当年连放屁也是番薯味的木子了,也不再“木”了,连大人教育娃仔都会说:“看看,看看,有木子一半好就了不得了……”“嫁给木是福哟……”更有人对“木”重新下定义,“木子”的“木”是五行中的“金木水火土”,有木,便有材,便有才和有财。大村人虽然不懂汉语修辞,却懂“木”的引申义,懂得生辰八字,相术手纹,前卜后卦。
那时,我内心十分感激木子,帮了一个天大的忙,也十分感激父亲乡亲们的慷慨相助。因此,每逢假期,回家拿钱拿物,都会挨家挨户走走,东家坐坐,西家聊聊,感恩感怀,给远离城市的大村乡亲带来一些奇闻秩事,我讲得津津有味,大家听得津津有味,乐乐哈哈。。大村的乡亲们淳朴得就像他们脚下的红土地。期间,木子没再做“土工仔”了,那次他把的钱给我之后,从信用社贷了款,回到村里养羊。母亲说:“木子是个好孩子”。后来我才知道上大学的大半费用都是木子给的。
木子的羊群放在村东头十里湾的草地上,那是寒水河畔,距村刚好十里路,建起羊圈,这是他辉煌而壮丽的事业,也是村人羡慕的事业。
我第一次背起行囊挥别家乡上大学时,是父亲和木子把我送到乡车站,我坐上开往县城的一辆小货车,安排妥当之后。他们欲回走时,他们发现路边的一幢小平房前聚满了很多人,唧唧喳喳地议论。平房前挂着金灿灿的圆形徽章,上烙着两个大字:储蓄。人们不懂得这两个字,更不懂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。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期期艾艾地费力解释,人们还是似懂非懂。老头急了,好久才从结巴的嘴里才蹦出:“银……银……银行—”两个字来,人们才明白与钱有关的地方。后来,圆徽章下面又多出一块白底黑字的木匾:寒水乡信用社。又相继贴出几张红艳艳的布告。人们才知道可以从里面贷款做生意什么的,但借的人不多,乡下人担心借得起,还不起,还不起可要被“抄家”的,这“抄家”是村潜意识里有的。木子不怕,他在自己心里盘算了一个多月,计划了一个月,觉得能行。就把想法告诉了父亲,父亲起初不同意,可是没有什么好差事让他做,只得任他。于是,不费周折,就从寻个小平房里捧出花花绿绿的大团结。不过,钱捧在手里还不热,就被乡里的干事带到很远的邻县一个牧场拖回两车咪咪咩咩羊羔儿。他便成了实实在在的羊倌。大村人对他这一举动,认为他大脑进了水,不种田挖地就是不务正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