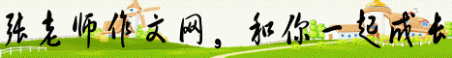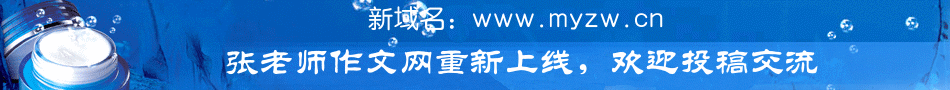核心提示:我把木子称为“木子哥”是在省城按揭买房的那一年,木子拿钱给我交了首付。叫了二十多年的“木子”,一下子改过来,嗓子眼硬生生的,感觉格外的拗口和别扭。因此,在众人的场合,我会把“木子哥”这三个字尽量加快语速,含糊不清,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到。而木子却能够在人声嘈杂中准确地听出来,这样没有人注意到我这敏感的...
我把木子称为“木子哥”是在省城按揭买房的那一年,木子拿钱给我交了首付。叫了二十多年的“木子”,一下子改过来,嗓子眼硬生生的,感觉格外的拗口和别扭。因此,在众人的场合,我会把“木子哥”这三个字尽量加快语速,含糊不清,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到。而木子却能够在人声嘈杂中准确地听出来,这样没有人注意到我这敏感的称呼,也就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个细节。他憨憨地对着我微笑或向我走来,而我叫这三个字之前也会在大脑里思付一番才含糊不清地吐出来。之前 “木子”的叫法很不礼貌,可我认为他不是我家的人,是一对傻夫妇留下的野孩子,不值得尊重。
“木”在家乡的方言的理解中是“呆”的意思,这名字听说是九生爷给取的。木子姓张,是岑黄姓氏大村里唯一姓张的人。据说,在那年岁里,一对傻夫妇因自然灾害流浪到大村乞讨。因为当时是大队集体制度需要劳动力,身为队长的父亲想让这两个四肢健在的夫妇也去参加劳动,说不能给他们白吃,用他们自己劳动换换,村人纷纷赞同,更有人高呼多分些任务给他们。大家以这样的方式接纳了这对流浪的夫妇。
他们住在大榕树下,用了几根竹子支撑地面,顶端斜靠在树干上,形成了三角架,比一个猪圈还大些,再从村后狼嚎山上刈些杂草,铺在上面避雨遮阳,成了他们的“窝居”。他们理顺成章成了大村大队的队员。夫妇俩少言寡语,终是默默地劳动。
男的本想住到庙堂里,觉得那土木结构的房子是他们理想的居所,但提出的话没说完,便惹怒了大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,人们高呼“孽债”,急得女的跪地求饶,才躲过“驱逐”的厄运。庙堂是大村的圣地,供奉土地神的地方,保佑大村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人丁兴旺。怎能容许他们与土地神共居一堂呢?
这对夫妇就是木子的爹娘,瓦解大村集体劳动制度的时候,木子已三岁多了。这一年的大村,发生了一件特大事件。一日清晨,这对夫妇双双死茅草房里,木子嘶哑的哭声引来了住在附近的九生爷。九生爷说:两人硬梆梆地躺在地上,身体卷缩,口吐白沫,翻大白眼,十分恐怖。擅长讲述的九生爷向人们讲述的时候,说得惊心动魄天花玉碎,吓得村童不敢听讲。人们便议论开来,有的说,榕树是千年的神树,他们住在树下侵犯了神,必遭罪罚;有的说,他们可能误食有毒的野菜;说到这便有人质疑,误食野菜应该三个都呜呼,咋就呜呼两个?有人解释:他们吃野菜把米饭留给木子吃……争论的同时也有叹息,这叹息也许是大村人给他们最深情的吊唁。村里的长老为他们举行简单的葬礼,葬到狼嚎山的密林中去。之后,人们便关注起小木子来,小木子才四岁多,大村人同情,可怜,可没有人敢收留他。
父亲把木子带回家时,是当日的黄昏,人们纷纷散去,秋雨飘飘洒洒的下着,秋风瑟瑟地抖落了一地的老黄叶,木子颤微微地蹲在树下,像个泥塘里爬出的泥娃娃,面无表情。父亲觉得他可怜,就带回来。然而,父亲的做法却遭到三公六婆们的反对,尤其是祖母。姑且多一张嘴吃饭不说,而认为木子是个灾星,死了爹娘,不吉利,进谁家谁家准会晦气。父亲只得解释:先让他住几天,再向乡里汇报,让乡里的人处理。然后把木子安顿到马房里,马房里已没有了马,木子就睡在木箱上的草垛里。祖母是刀口嘴豆腐心,还是给了一床旧棉絮,打一碗小米饭给木子吃。反对声浪缓和了下来,母亲在一旁默不做声,这是男人和父辈们的事。父亲也是黑着脸,话不多;祖母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打扫马房。